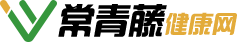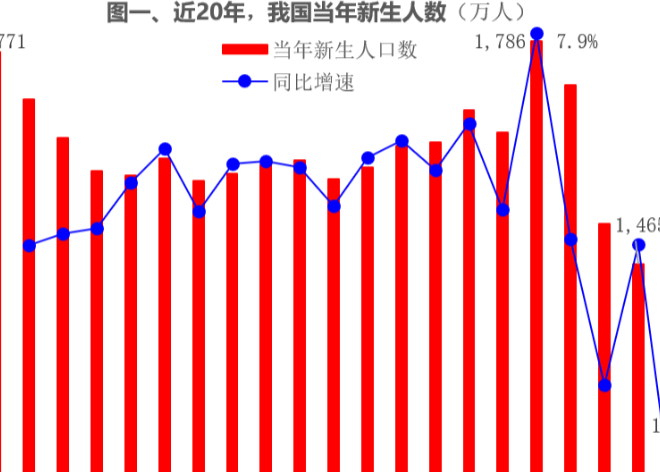1990年,患有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的4岁小女孩德西尔瓦参与了一项里程碑式的临床试验,从死亡宿命逃脱的她,成为基因疗法具有现实可能性的最大证据支持,大大鼓舞了相关研究者。
然而乐观与激进的试验,蒙蔽了警觉基因疗法危险性的双眼。1999年,患有鸟氨酸氨甲酰转移酶缺乏症的杰西·盖尔辛格接受基因疗法4天后,因多器官衰竭死亡。调查推测,这或是由其免疫系统对递送载体腺病毒产生了强烈反应所致。
无独有偶,“杰西事件”发生次年,用于治疗X连锁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症的基因疗法,导致了T细胞急性白血病的发生。原因是γ逆转录病毒整合到特定的基因组位点,导致原癌基因上调,进而细胞癌变。
基因疗法发展自此踩下“急刹车”,业界自省同时,也展开了对于更加安全的递送载体的探索。
“好病毒”腺相关病毒(AAV)进入了人们的视线。由于免疫原性低、表达稳定以及递送效率高等特性,AAV也是当下应用最广泛的病毒载体。
然而,AAV并非绝对安全,相关争议也不少。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评价:“研究AAV就像剥洋葱,越剥眼泪越多”。
1
选择AAV的理由
AAV是单链DNA病毒,并无自主复制能力,需要借助腺病毒或疱疹病毒等病毒辅助,才能完成复制,在这一过程中还可以抑制致病的辅助病毒,相当于病毒的“寄生虫”。
在现有认知中,AAV为各种病毒载体中免疫原性最低,几乎没有毒性,无致病性。在NIH对于生物技术制品的相关评级中,AAV处于最安全等级。
出色的安全性是目前AAV成为体内基因治疗的首选载体的主要原因之一——几乎90%的基因治疗临床试验都在使用AAV,针对的疾病包括但不限于B型血友病、LPL缺乏症、囊性纤维化、肌营养不良、帕金森氏病和HIV。
除此之外,AAV还具有一个很大的优势:13种原发性AAV血清型和100多种不同的变种,使其能够很好地定位于特定组织,例如视神经、中枢神经系统或肌肉等。
2017年,FDA批准了美国首款基于AAV载体(AAV2)的基因疗法Luxturna,用于治疗疗双等位基因RPE65突变相关的视网膜营养不良的眼科疾病。这是真正意义上,FDA首次批准用于治疗遗传性疾病的基因疗法。与后续其他基因疗法一样,Luxturna定价同样昂贵,单眼治疗费用高达42.5万美元。
但若论全球首款AAV基因疗法,则还要再向前追溯。2012年,EMA批准了基于AAV1载体的基因疗法Glybera,通过向患者骨骼肌递送脂蛋白脂肪酶基因,从而降低患者胰腺炎的发病率。一针百万的定价,加以过于狭窄的罕见病市场,使得Glybera最终于2017年黯然离场。
第三款则是来自诺华的Zolgensma,用于治疗脊髓性肌萎缩症(SMA),使用AAV9递送活性运动神经元存活基因1(SMN1)以取代无功能的突变SMN1,于2019年获批,定价212.5万美元。
2
三大风险争议
8月,诺华报告两名儿童在接受Zolgensma治疗后,因急性肝功能衰竭而死亡。截至报告之际,全球范围内已有超过2300名患者接受了Zolgensma治疗——这是该药上市以来,首次报告急性肝衰竭的死亡病例。
但这并不是首例,基因疗法与肝毒性的关联绝不仅此。
在过去两年中,安斯泰来的基因疗法AT132的试验被多次暂停,原因之一即是摆脱不掉的严重肝毒性副反应。该药物用于治疗X连锁肌小管性肌病,使用AAV8载体递送肌管蛋白基因至骨骼肌,从而增加组织中肌管蛋白的表达。
2020年,三名儿童在接受了高剂量(3x1014vg/kg)的AT132后死亡,均发生了肝功能衰竭,试验一度暂停,当年末,FDA准许安斯泰来重新开始试验。考虑到先前接受低剂量(1x1014vg/kg)的AT132治疗组中患者并未出现类似肝功能问题,安斯泰来一改激进策略,用药量降至略高于先前最低剂量组(1.3x1014vg/kg)。但结果并未如其所愿,2021年又有一名儿童出现肝功能异常后死亡,当年9月,试验再度暂停。(参考资料:基因治疗安全性问题频出,Astellas何时能上岸?)
AT132引发了对高剂量AAV载体的肝脏风险的审视。
事实上,早在2018年,就有相关研究指出,AAV载体对肝脏具有高亲和力,会天然富集在肝脏细胞中。这一事实导致,若只是靶向肝脏,低剂量的AAV载体即有效,但若是靶向其他部分,要达到有效浓度,全身给药时的AAV载体剂量必须大幅度提升,以及考虑到载体空壳率,患者的实际肝脏负担更重。
与高剂量相关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,是免疫应答。
一个成年人身体中仅有大约3x1013(30万亿)个细胞。成年人较为容易容忍与细胞数量近似的AAV载体数量,当剂量超过100万亿AAV载体剂量时,免疫反应很可能发生——干扰病毒载体与细胞的相互作用,严重阻碍基因疗法的治疗过程。
16年前,在首个靶向肝脏,用于治疗血友病B的使用第一代的AAV2载体的基因疗法试验中,就有相关风险报告。
从这项试验中可以看到,约70公斤的成年人体可以很容易耐受AAV2载体剂量4x1011vg/kg全身注射(大约28万亿AAV2颗粒),但当剂量提升至5倍达2x1012vg/kg(大约140万亿AAV2颗粒)时候,CD8+T细胞对载体的衣壳蛋白产生了应答,使得AAV载体在传导细胞之前,已经被人体的免疫系统清除。
第三个争议即是AAV载体或会增加患癌风险。
2020年,UniQure的针对血友病的AAV基因疗法使得一名患者患上肝细胞癌(HCC),作为III期临床的一部分,这位患者于2019年末接受了递送IX基因的AAV5载体的注射。
与此同时,另外一项使用AAV8载体递送FVII基因,治疗A型血友病犬的10年随访研究结果也引起业界关注:五只接受治疗的狗中发生了AAV整合,以及整合后的细胞增殖。
这一发现让AAV的安全标签岌岌可危。然而在后续调查中,发现UniQure试验中的这位HCC患者,原本就患有慢性乙型和丙型肝炎感染,其本身就是HCC高发患者,因此发现的肿瘤或与AAV治疗无关。此外,第二项试验,虽然表现出AAV整合,但是随访中并未发现有肝癌或者肝功能障碍现象。
因此,AAV载体是否真的会致癌,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。
但频发的安全事件仍让人忧虑:有研究表明,约1/3的AAV基因治疗试验存在“治疗出现的严重不良事件”。无论如何,FDA是“坐不住”了。
3
对研发热情的谨慎平衡
2021年,FDA召集了一个专家小组,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上讨论了基因治疗的安全性——癌症风险,以及在动物实验和人类中观察到的对肝脏和大脑的毒性。
在讨论癌症风险时,专家们花费了大量时间权衡动物测试的结果。例如,在小鼠中,观察到了该类基因疗法在给药剂量较高、特别是幼龄给药的情况下,致癌风险较大,而目前在猴子、狗等大型动物的实验中尚未观察到此类风险。结合上述A型血友病犬的研究,FDA专家认为,致癌风险仍然是理论上的。
FDA专家建议,为了更好评估AAV风险,有必要延长动物实验观察时长,因为“DNA的损伤可能在一年乃至18个月后才出现”。同时,应当“长期跟访接受治疗的患者,以确保即使是罕见的不良反应也能被观察到”。
另外,对于临床研究,专家们提出了“通过在人类细胞系上开展研究等,实现更接近人体实际环境的研究”。这与辉瑞观点不谋而合,其在向FDA提交的公开评论中指出,应减少在动物体内研究基因整合的试验,除非有“与人类有明确的因果关系”的证据出现,声称使用人类细胞系评估风险的试验更有参考价值。
癌症风险或许是理论上的,但是肝毒性却是切实存在的。不过对于究竟如何规避肝脏风险,FDA暂时还未提出具体建议,只是表示“研究人员应当更全面地评估以及筛查患者先前存在的肝脏疾病。”UniQure就是先例。
值得注意的是,先前试验已表明,在高剂量注射时,较为容易出现严重的肝脏副反应。尽管如此,FDA专家还是反对设置基因治疗剂量上限。有专家表示:“基因治疗剂量构成难以具体表征,因为其中或含有与治疗DNA无关的物质。”
— 总结 —
不得不说,安全性已经让基因疗法的研究停滞、倒退了好几次。在科学研发上,傲慢与轻视带来后果是将是难以承担的惨烈,安全性是必须迈过的门槛。
我们需要谨记,自然界中,AAV载体并没有向可递送基因的载体的方向进化。对其改造与试验必然要十分谨慎、小心。值得庆幸的是,尽管AAV载体存在一些争议,但只要不给予其天文数字的高剂量,就能尽可能减少一些安全性风险。
当然,对AAV载体的改进从未停止:下一代的AAV应当在提升疗效时,所需剂量更小,对人类的特定细胞与器官的生物选择性更高。
正如克睿基因董事长徐元元所说,选择AAV的理由在于它的“可塑性”,让其从一个“好病毒”变成“更好的病毒”:“通过工程改造或者计算生物学,设计出新的AAV血清型达到在装配过程中增产、提高转导效率、避开体内免疫中和、减少肝毒等若干目标,特别是靶向特异性:如心脑肝肌等全身系统性注射的组织器官、眼耳等局部注射的组织器官、造血及免疫等细胞,要根据递送的不同目标来进行体系化的设计和评估。”
十多年前的沉寂之后,基因疗法以破竹之势发展。截止今年上半年,全球进展中的基因疗法开发管线已超过2024个,仅在8月,就有两款基因疗法获批。而根据相关预测,到2030年,将会有40-50种新的基因疗法获批临床。
载体是基因疗法成功的关键之处,也是未来技术进步、成本降低的突破点。我们期待有更好、更安全的基因疗法出现。
文章来源:药智新闻
推荐阅读:
异维A酸让油腻的皮肤变清爽,一步到位?服用前要知道这些(上)
异维A酸让油腻的皮肤变清爽,一步到位?服用前要知道这些(下)